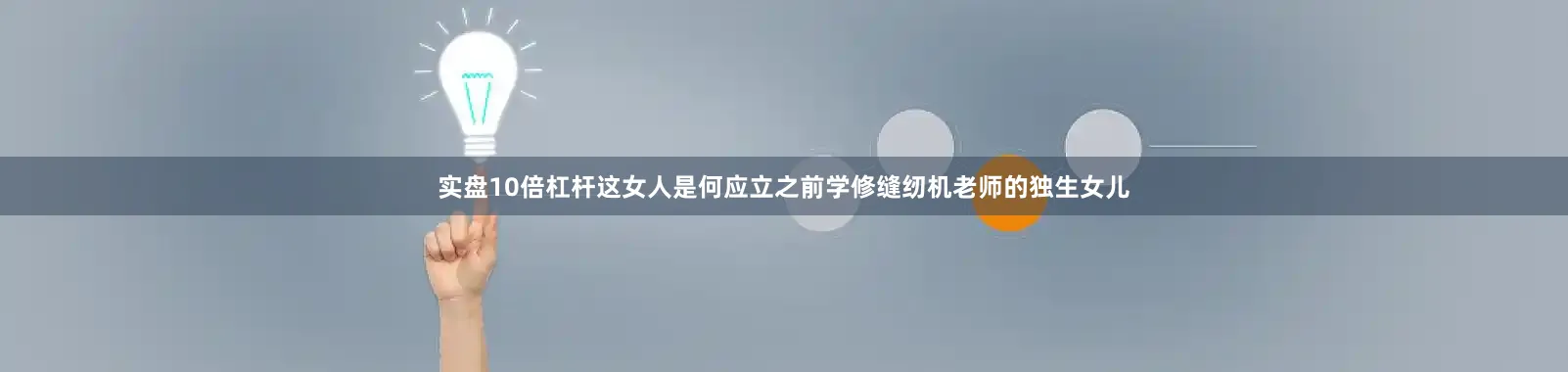
我大约16岁时,为挣钱去大城市求艺,天真的我在家乡石桥附近几个乡镇画商品画挣钱。
我肩挂起简约画具,向镇旁边的红斗梁山爬去。爬山前,我望向山峰,山峰被白云时遮时露。近2小时爬上山顶,俯瞰山下石桥镇,石桥镇被雾海淹没,心里难免有一丝恐慌,随即转身在山顶弯来弯去的小道上行走。
到达佛楼乡,经我在供销社自我推荐,接下了画门市柜台上宣传的五金百货产品图案的活儿。画图时,我打听一位叫潘霞的石桥女人,她带着两个娃子远嫁到这里,平坝嫁到山上,属于穷嫁,穷嫁总有穷嫁的故事。
我打听到潘霞阿姨,她正好一人在家,很热情地给我煮了中午饭。她除了跟我说话或面对我时带点笑容外,就是一脸愁云布满在脸上。她在厨房锅灶下叉柴时,燃烧的柴火红光映着她的脸,那脸愁红得如夕阳发紫,我敏感到这愁的表情是因为我的到来,推开了她紧闭的石桥记忆大门,勾起了她那不堪回首的片段。
石桥方圆约30公里,就是我童年、少年能看见、触摸着的世界,这世界对我是真实的,而非画报书上展示给我的虚拟世界。
我与小朋友最爱去的地方是食品站、粮站、供销社、农机厂。农机厂有个做秤的工房,工房像一个半新半旧的教室,窗子是一长排木竖条,里面有几个人在操作,打磨秤杆,用小锤敲打银丝嵌进秤杆,来标示“浅”“两”“斤”的标示和间隔,这轻微的锤声有时连敲打的人都听不到,这微音就跟街西边的铁匠铺时快时慢的叮当叮当铁锤声成了鲜明的对比。
展开剩余69%做秤师傅名叫何应立,他个子不高不矮,头大,五官突出,特别他长有一张大嘴,却少言,壮实的体形如他长期试的秤砣一样,厚重结实。由于他被单位派到达县五金厂学会做秤这技能,回乡后自己埋头苦干、勤奋认真,做的秤不但满足了本乡镇,还扩散到邻县的乡镇。这秤匠工坊就不得不招兵买马,收学徒,学徒中一位是女的,这女人是何应立之前学修缝纫机老师的独生女儿,老师曾多次交代何应立说:“多关心小芬,把她当妹妹看。”
小芬虽算不上镇上漂亮的女人,却聪明伶俐,善说善笑,又爱打扮,给做秤安静的工坊带来了活泼气氛。小芬不像学徒们称何应立为老师,开口闭口叫何哥,这长期娇滴滴的呼哥声,如一股暖流渐渐渗透进憨厚何应立的心田。时间一月一月过去,他俩走近了,近得在夜晚榕树下、高粱地相约。
每次相约后,何应立总是在回家路上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很内疚这样下去对不起贤惠勤劳的老婆潘霞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又怎面对街坊邻居,特别是老师。他更深深知道小芬是有夫之妻,而且是军婚,触犯军婚的后果他是知道的。
对自己无数次警示,又怎能挡住“哥来哥去”的甜蜜叫声和相约肌肤相融拥抱的刺激。这难防的“破墙”自然产生了小芬怀里有婴儿之果。
婴儿在肚里一天一天长大,何应立和小芬一天一天恐慌,那段时间做的秤数量减少,返工又多。农机厂领导有所察觉,何应立与小芬超出平常人的暧昧,曾警告过他两次说:“何应立,你父亲虽是地下党员,但你也不要犯男女关系错误,小芬是军婚,破坏军婚你应知道后果的。”这警示已经晚了,何应立一边否认,一边与小芬商量,为不露一丝风声,就不去镇上中西两医院,在赶场天找了江湖摆药地摊的人,开了几副打掉婴儿的中药。
一周后,石桥公社被县上公安警车拉起的呜呜长鸣声而惊恐,小芬家门外人群闪开了道,警车开进停下,即下来几位公安,其中法医2位。
第二天,何应立双手被戴铁链推上车带走。不久,何应立因破坏军婚罪,使小芬吃药致死,被判刑15年。
这件事受到特别打击的是何应立的老婆潘霞,潘霞被这措手不及的家丑事,使她在镇里丢尽了脸面,一年后她带着幼小的两个孩子改嫁到山上佛楼乡,从此离开她生活几年的故乡。
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采访石桥冉心龙妻子时,她其中说到:“后来石桥与佛楼乡通车,她去过一次,本是当天去当天回,但潘霞抓到她手不放,非留她一宿。潘霞改嫁的是一位教师,两孩子就改姓跟教师姓,教师老婆早去世,留下4个孩子,所以潘霞是带着6个孩子。有年潘霞的孩子当兵入伍,从佛楼乡下石桥镇统一上车,在等车中大家看到他,一下在石桥镇传开,何应立孩子小名叫爪爪,大家都围爪爪关心问长问短,爪爪原几个童伴也跑来告别。”
爪爪几年兵役回来,分配到达州达钢。目前何应立一女一儿在达州早退休,潘霞80几岁在独居。40多年前,何应立出狱后,首先去看望小芬父母(师傅师娘),但小芬父母在独女小芬走后,相继去世。后来何应立在石桥铝合金门厂做零活,找了白衣乡一个少妇结婚,没多久何应立病逝,潘霞领着儿女一起回石桥为何应立办理丧事而操劳。
2025 - 7 - 2
来源:画家冉崇君
发布于:四川省启泰网-股票配资官网-股票日内配资-配资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